|
记得有一次,一位从驻苏联使馆回国休假的政务参赞来看望大家。他见我是新人,非常关心,还当场用俄语考了我一下。最后,他希望我成为一个“незаменимый эксперт”(不可替代的专家)。我不知道“эксперт”(专家)这个词,没听懂。他提示后,我请教说,专家不是叫“эксперт”吗?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乐呵呵地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周总理非常关心边界谈判的进程,从谈判方针到礼宾安排都亲自过问。谈判期间,凡遇重要情况,团长都直接向总理电话请示或书面报告。为推动谈判,周恩来总理向苏方传话,指出:争议地区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你们不承认,我们就达不成协议。苏方曾提出两国总理再次举行会晤的建议,我方以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尚未履行为由予以回绝。 1969年10月再启边界谈判的直接背景是,当年3月在中苏边境黑龙江省虎林地区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两国关系空前紧张。 开始出席对外活动时,我一般都提早5分钟到场。老同志马上提醒我,像这样的集体活动,至少要提前10分钟,不能让别人等。如是工作人员,还应更早一些,先检查一遍场地或车辆等有无问题,然后迎候首长。如果领导来晚了,不能直接催叫,要通过秘书;即使晚到了,也不能说迟到,而应向对方解释说,领导有急事耽搁了。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终于初步掌握了两国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症结所在。领导还特意组织全团进行边界业务学习,进行考核,由我主讲,老同志提问补台。 苏方不承认两国总理已就此问题达成谅解,拒绝讨论临时措施协议。后来,苏方作了妥协,同意进行讨论,并交换了几次方案。但因双方立场各异,怎么也谈不拢。双方分歧、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 苏方之所以不承认两国总理就争议地区问题达成的谅解,据说是因为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没有通过,认为柯西金由于不了解情况,上了周恩来的当。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没有料到,一谈就是9年,被称为“马拉松式谈判”。 为了培养我,领导不断给我加压。除了管理资料外,新增了办案业务,具体处理涉及边界历史等问题的文章、书籍及地图。后来,又让我担任谈判代表团的联络员,协助一位老同志负责对外联系。因为我最年轻,一有会议或出差机会,他总是带着我去见习。与此同时,上级对我工作上的要求十分严格,不容许有半点疏漏。 为了打破僵局,双方都做了一些努力。苏方建议用对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的地段”、“需要核定的地段”或“被争议的地区”等措辞来取代“争议地区”的概念,我方则以违背两国总理谅解为由未予接受;中方也提出过折中方案,建议采用双方对边界线“划法不一致的地段,即有争议的地区”的措辞,而对方要求去掉后半句,中方不同意。 边界谈判的原始材料、地图、书籍很多,“文革”中又搬了几次家,后来都被杂乱地堆放在一个黑屋子里。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先进行了一番清理,然后把所有资料分门别类登记造册,贴上标签,并做了卡片索引。领导肯定了我的起步工作,要求再深入钻研,尽快成为中苏边界问题专家。 北大毕业后,经过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和北外回炉进修,我于1973年3月进外交部工作。这是“文革”以来外交部第一次接纳大学毕业生,各级领导都很重视。 我们代表团有一个北京图书馆的特殊借书证,可以借阅“文革”中被视为“禁书”的外文书籍。利用工作之便,在查阅有关边界问题图书的同时,我借阅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俄文长篇小说。平均一个月一部,主要是泛读,提高阅读能力,扩大知识面。有一次,我看北图的工作人员不懂俄文,还趁机借了法国司汤达著的《红与黑》俄文译本。这部小说在当时更被看做是“毒草”,所以我平时把它锁在抽屉里,没人时再拿出来看。 (责任编辑:admin) |
| Tags:中苏边界谈判:周总理向柯西金解释“争议地区” |
栏目分类
创业项目相关信息
热门创业项目文章推荐
-
“厕所野战”女星哭诉:他带我
近日,闹得香港满城风雨的“厕所野 -
2018年小本创业,很多人看不上
许多人想创业,干一番事业,但又苦 -
小伙景区玩PS卖金秀贤合照 月
6月19日,有微博网友爆料,说自己 -
首届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今天拉
湖北,黄石,新闻.东楚网是您了解黄 -
黄金酥豆腐 人见人爱
市场信息报 -
10个小成本创业项目赚足商机
小成本创业做什么好?现如今小本创 -
电子商务带动新疆疏附县群众创
一手拿锄头、一手握鼠标,新疆疏附 -
78创业日3.6亿大派送 创业圆梦
78创业日3.6亿大派送 创业圆梦省钱 -
大学生创业项目方案
大学生创业项目方案,青岛有个14岁 -
小生意,赚大钱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在走向人
广告赞助商
创业项目文章阅读排
- 1、功能饮料功能饮料市场,在过去一年不断有
- “厕所野战”女星哭诉:他带我进去 亲我(1)
- 女孩小本创业好意见 一年600头猪纯利润多少
- 微立拍品牌投资创业快速成功
- 2018年小本创业,很多人看不上眼的冷门高利润
- 创业投资应避免一哄而上(感言)
- 小伙景区玩PS卖金秀贤合照 月入上万羡煞网友(
- 昆明高新区构建创新创业全链条孵化企业500多
- 女辅导员与在校男大学生隐婚 放弃留校(图)
- 首届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今天拉开帷幕
- 淮北市首届青年创客暨电子商务创业大赛圆满落
- 一路飘香小吃车,小本投资大生意!
- 涉县:“小额借款圆了我们的创业梦
- [财经]大庆首家互联网+创业咖啡开业,开启地
- 小本创业需谨慎 创客”拣错铺 半年亏20万
- 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去留北京又做选择
- 第三次!火箭海外引援又受挫 黑山天才已赴俄
- 黄金酥豆腐 人见人爱
- 解读四川小本投资冒菜加盟项目零风险的计划书
- 仔皇煲创始人:连锁快餐店怎样创业?
◎ 主页 > 创业项目 > INTRODUCE
中苏边界谈判:周总理向柯西金解释“争议地区”
特别说明
此处放横条广告
◎ 阅读说明READ EXPLANATION
☉推荐使用第三方专业下载工具下载本站软件,使用 WinRAR v3.10 以上版本解压本站软件。
☉如果这个软件总是不能下载的请点击报告错误,谢谢合作!!
☉下载本站资源,如果服务器暂不能下载请过一段时间重试!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请到本站论坛去咨寻,我们将在那里提供更多 、更好的资源!
☉本站提供的一些商业软件是供学习研究之用,如用于商业用途,请购买正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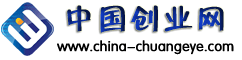


谈谈您对该文章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