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生长于农村社会的农民来说,尤其是那些20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人,长期生活在低度市场化的环境中,对市场规律很是陌生。要知道市场如何运转,并驾驭市场,对他们来说,难度尤其大。而且从赵湘几次失败的经历看,长期生活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使他们身上有一些和市场不合拍的东西。他们更多的是按照熟人社会的逻辑去行事,更重情谊和信任关系而不是理性的“精确计算”,不愿忍受和不讲情面的老板共事,宁愿不挣钱也不愿受“气”,为此,他们也会错过不少市场机会和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机会。 幸而时代给了早期进入商海的农民一些机遇。在商品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那些越早进入商海的农民越发容易成功,即使此时的他们不太懂得市场经营,他们没有多少资金和关系资源。他们能够在市场环境较为宽松的条件下,积累一定的信息、资金和人脉,掌握某些市场规律,习得驾驭市场的某些能力。这些人的成功,使得很多后继者可以在前者的帮助下,进入到市场,参与市场竞争。 对于后继者来说,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的关系资源就成为了他们能够进入城市经商,从而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保障。赵湘便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哥哥帮着他照顾孩子,是他能够低成本进入到市场的前提。 从小舅子到侄子,再到嫂子的弟弟,帮助他进入到市场的熟人两个手都数不过来。他们或者为他提供资金、或者为他提供技术,信息。正是依靠这一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他拥有了很多次向上流动的机会。虽然赵湘没有成功,但是在农村社会中确实也出现了不少农民创业成功的故事,从一个摊贩到一个饭店,从一个厂仔到一个厂长或者店铺老板,从一个建筑工人到一个工程老板等等。 另外,让笔者更为感触的一点是:即使经历了很多次失败,在赵湘的身上,笔者依然感受到了一种从容。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不需要自己太操心。赵湘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也不错,3000多元一个月,有三险一金,加班或者帮助学院的老师布置会议室,还能挣点外快。妻子做家政,一个月收入4000元左右。他们省吃俭用,开始计划在家里的县城买房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有退路的。等到城市待不下去了,他们还可以回农村种地,可谓“家里有田,心中不慌”。 对于最后一点,或许是大多数从事商业经营的农民能够较为从容的共同原因之一。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土地为农民提供最基本和最底限的就业、生活保障。正是因为农民有退路,使得他们能够更为从容的面对市场中的风险。此外,正是农民有退路,也使农民更加敢于不断尝试新的生意,或者在同一个生意中不断做出新的尝试,从而找到新的机遇,适应市场的动态变化。 我们知道,市场是动态的,个体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就要经历不断的试错。试错的结果不一定是理想的,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是不进行试错,就可能完全丧失竞争力,被市场淘汰下来。对于资金能力和社会资本、信息获取能力都更弱的农民来说,这成为了他敢于不断试错的重要资本。 正是因为土地集体所有和熟人社会的存在,使得我国很多农民在城市拥有更多向上流动的空间和机会。集体土地和乡村社会使得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有了喘息之机。一次创业失败之后,农民返回家乡养精蓄锐几年,再出去重新创业或者打工。在我们周边,一些农民总是反反复复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穿梭,这样的故事也并不少。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农村渐进城镇化的内在“秘密”。 在一些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农民或许同样可以依托熟人社会参与市场竞争,他们也许还可以依托于土地私有制,抵押土地而实现资本积累,从而提升自己在城市创业的竞争力。但是这可能仅仅是有利于部分拥有土地的农民,对于那些失去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们不仅没有这么多创业的机会,也没有这么多创业的空间;一旦在城市创业失败,就只能进入到城市的贫民窟,有可能永无翻身之日。他们对于创业成功与否就表现得更为焦虑,在投资过程中也有可能更为极端和孤注一掷,也就很难在失败之后感到如此从容。 当下农民在城市创业的空间越来越小 不过,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国农民在城市拥有较大的创业空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创业,是因为卖方市场的存在,而且整个市场秩序还在快速变革,城市和市场拥有大量的灰色空间,城市服务业以及一些相对低端的行业管理还很不正规。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可以基于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等,在这些灰色空间中找到各种创业的机会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在这个阶段,农民进入市场的门槛很低,城市市场中也还有大量边缘性的、灰色的创业机会。 但是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为了塑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国家对市场和城市的管理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城市和市场的规范化意味着灰色空间减少,一些低端行业也在正规化。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环保政策的推行、城中村改造,很有可能导致这些地区商铺经营的成本上升;文明城市的建设,城市对流动摊贩的包容性降低,很多农民就不得不从城市的边边角角中被挤出去;原来家政服务都是非正规化的,点对点的,现在的家政服务需要注册公司,而且开始进行更为严格的资质审查,这不仅会增加成本,还会使准入的门槛上升;等等。 在这一形势下,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农民靠一个摊位而发家的故事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农民通过在城市经商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趋势呢?是欣然接受,还是强烈反对? 笔者认为,这都不可取。产业升级和良好营商环境的塑造,是中国在日益焦灼的世界市场竞争或者说贸易战争中能否胜出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但是同时也要明确的是,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农业领域能够消化的劳动力是有限的,还有大量的农民需要依靠在城市中就业和创业来实现家庭的稳步发展,因此我们的城市化步伐又不能太急和太快,不能以太过直接和粗暴的方式推进这一过程,使得农村社会完全没有喘息的空间。这是我们理解城市与农村关系的前提,也是我们思考很多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前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要以什么样的速度和方式推进环保政策,推进城市的正规化、标准化和市场管理的制度化?我们是否要推行农村的规模化经营,如果要推行,我们如何安置被农业挤出来,但是又不被城市吸纳的劳动力?我们如何看待养猪等涉农产业对于当前农民就业的意义,对于我国产业升级的意义?我们是否要推进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之下,土地抵押所获得的一点资本对于解决农民创业问题能有多大帮助?资本能力是不是影响农民创业问题的最重要因素?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要在当前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村社会的关系中进一步寻找。 (李婷,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社”,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
责任编辑:朱凡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农民经商,熟人社会,市场经济,城乡关系 相关推荐 评论(0) (责任编辑:admin) |
| Tags: 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 600870 heize sweet dream 传颂之物虚伪的假面 flower road 小地鼠的花园 senorita |
栏目分类
创业故事相关信息
热门创业故事文章推荐
-
4月封面故事:捕梦者徐和谊
中国梦的北汽篇,落在徐和谊的棋局 -
范逸臣演绎 80后创业精英
“尚影周”沙龙现 -
吉林省大学生创业明星分享成功
吉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进校园宣 -
我的创业故事:威海90后女大学
外表时尚文艺,内心却怀着创业的激 -
二手车买卖背后的创业故事
众所周知中国二手车交易市场每年有 -
中国梦·西藏故事:益西江措百
他拥有跌宕起伏的人生,30多年来, -
奇瑞重工创业故事:自强不息的
奇瑞重工创业故事:自强不息的创业 -
【品牌故事】三添创业五十载浓
作为我国四大食用油料作物之一,芝 -
创业20年 海澜之家正在讲述新
【亿邦原创】 海澜之家正在讲述一 -
青春虹讲堂分享“奋斗的青春最
4月25日 ,青春虹讲堂第十讲之我的
广告赞助商
创业故事文章阅读排
- 揭秘北京最靠谱的私人侦探
- 4月封面故事:捕梦者徐和谊
- 何帆丨失败的故事:大数据下的创业与创新
- 武进万达健康产业创业励志故事
- 范逸臣演绎 80后创业精英
- 主播麻宁辞职创业不犹豫
- “发现双创之星”活动走进江苏 讲述双创好故
- 吉林省大学生创业明星分享成功经验
- 招财猫讲述一位90后成功创业的故事
- 夏季亭、陈龙飞:两代校长的创业故事
- 从时代广场到硅谷创新圣地:90后分享Solo创业
- 创业创新转型升级典型
- 创业故事:在校女研究生开“织梦编织吧”
- 青年台商成都创业“法宝”
- 潍坊80后小伙辞职创业:从饭店老板到月入上万
- 利川红伶汇代理商仇鸾刚的创业故事
- 大学生团队用漫画开拓创业路 微博转型办工作
- 创业故事:天地壹号陈生谈做快消品的诀窍
- 新媒体创业借力互联网 项目聚焦吃住行接地气
- 我的创业故事:威海90后女大学生返乡创业
◎ 主页 > 创业故事 > INTRODUCE
农民创业的难和易:从一个农民在城市经商的故事说起(2)
特别说明
此处放横条广告
◎ 阅读说明READ EXPLANATION
☉推荐使用第三方专业下载工具下载本站软件,使用 WinRAR v3.10 以上版本解压本站软件。
☉如果这个软件总是不能下载的请点击报告错误,谢谢合作!!
☉下载本站资源,如果服务器暂不能下载请过一段时间重试!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请到本站论坛去咨寻,我们将在那里提供更多 、更好的资源!
☉本站提供的一些商业软件是供学习研究之用,如用于商业用途,请购买正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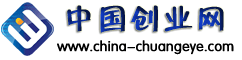



谈谈您对该文章的看